摘要 大部分研究者在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時,重點分析的是全國或全球的條件和刺激因素。他們將經濟繁榮與地理、人口、自然資源、政治發展、民族文化或者官方政策等因素相聯系。還有一些研究者選擇從產...
大部分研究者在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時,重點分析的是全國或全球的條件和刺激因素。他們將經濟繁榮與地理、人口、自然資源、政治發展、民族文化或者官方政策等因素相聯系。還有一些研究者選擇從產業層面來做出解釋,試圖解釋為什么某些區域要比其它區域更加繁榮。但歸根結底,就業機會并不是由社會、政府或者行業所創造,而是由企業或企業的領導者所創造。決定花錢與否、投資與否以及雇傭與否的終歸是企業家和企業。因此,本文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采取的是相反的方法,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即從企業和經理人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站在這一有利角度,本文發現,不同的創新型態會對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產生全然不同的影響。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視角讓企業家、決策者和投資者能夠開展前所未有的合作,一同去創造極有可能實現持續繁榮的環境。我們認為,公司層面存在一個完善的投資和創新模型,該模型能夠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繁榮,它能夠對過往的成功做出解釋,也能夠給利益相關者指明未來的方向。
創新的種類
我們的模型將創新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因為大部分的投資都流向了創新。創新,依次又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我們稱之為“持續創新”,其目的是對產品進行更新換代。這類創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能夠保持住市場的活力以及競爭力。人們在市場上看到的大部分變化都屬于持續創新。但是這些創新是通過自然替代來完成,即,如果一家企業成功地向其現有客戶銷售出一款更好的產品,客戶便不會再購買舊款產品。在三星推出其旗艦智能手機的改良版后,舊版的銷售量迅速下滑。當豐田說服消費者購買混合動力車普銳斯后,消費者便不會再購買凱美瑞。因此,投資持續創新很難在相關公司內部創造凈增長。同樣,持續創新也幾乎不可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進而促進宏觀經濟增長。
第二種類型叫做“效率創新”,該類型幫助企業實現以更少的成本獲得更多的產出。效率創新使得企業能夠以更低廉的價格制造或銷售既定產品或服務。例如,沃爾瑪零售模型就是一種效率創新。在將同樣的商品銷售給相同的顧客時,沃爾瑪的價格能夠做到比梅西這樣的傳統商店低15%,庫存能夠降至梅西商店的一半。在每一個高度競爭的經濟體制中,效率創新關乎企業的生死存亡。但是,由于該類型本質上追求的是低成本高產出,因此效率創新必然會削減工作機會,亦或導致工作崗位被外包給更有效率的供應商。除了有助于實現低人力高產出外,效率創新還能夠提高資本效率,改善現金流。
第三種類型是“市場創新”,在大部分行業的初期階段,他們的產品和服務非常昂貴且不易獲得,只有富人才有能力購買和使用。市場創新使得最初的產品和服務變得足夠便宜、更加容易獲得,從而最終贏得全新的客戶群。T型福特汽車、個人電腦、智能手機以及網上股票交易都是市場創新的例證。由于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負擔得起這些產品,創新者們就需要雇傭更多的人來從事制造、銷售和服務。由于市場創新簡化了產品、降低了成本,原本用于持續創新的供應鏈就不再適用。為了創造一片新市場,建立全新的供應網絡和配送渠道就變得非常有必要。市場創新者創造了新的增長以及新的就業崗位。
市場創新的投資要求具備兩個條件:一位能夠發現顧客潛在需求的企業家,以及一個經濟平臺的存在(指某種使能技術亦或商品或商業模式上的某個特質,能夠給規模經濟帶來顯著優勢)。例如,肯尼亞的M-Pesa服務,憑借無線通信平臺,讓用戶能夠通過手機轉賬而無需去傳統銀行開設賬戶,這在原本很少有人使用銀行服務的肯尼亞大獲成功。2007年,在M-Pesa發布之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肯尼亞人使用銀行服務;現在,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肯尼亞人都在使用銀行服務。與此同時,南非的電信巨頭MTN針對“非消費者”推出低價手機,借此整合了非洲大陸的通信基礎設備,在移動電話革命中拔得頭籌。
任何強勁的經濟在任何時期都會兼有以上三種創新類型。但是唯有市場創新能夠增加固定工作崗位,最終創造繁榮。通過將目標瞄向非消費,市場創新將發展中國家的弱勢(民眾多種未滿足的需求)轉化為優勢。在此過程中,市場創新創造新的價值網絡,開發新的潛能,制造持續的就業機會。這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因為創新者們會進一步探索更為隱蔽的非消費機會。
市場創新是如何運作的
我們此前的研究似乎表明,對于每一個獲得巨大增長和繁榮的國家來說,市場創新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戰后的日本也許是最好的例證。二戰期間,日本經濟被戰火夷平,因此,日本在很多方面所面臨的挑戰與其說是白手起家,倒不如說是重建。日本重建所取得的成功常常被歸因于民族自豪感和堅韌的職業操守, 或者諸如國際貿易工業部這些政府機構的遠見,亦或科學與工程學教育的卓著。但是,最近幾十年間,日本的經濟一直停滯不前,這些解釋逐漸失去了它們的說服力。回顧過去,對于日本戰后經濟增長更具說服力的解釋,應該是其在摩托車、汽車、電子消費品、辦公設備和鋼鐵領域的市場創新。
回想一下日本的摩托車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有超過200家摩托車制造商,本田、川崎、鈴木和雅馬哈從中脫穎而出,在國內外引領者摩托車行業的發展。這四大摩托車公司并不是從行業既有的領導者手中爭奪市場份額。他們選擇將目標市場瞄向了非消費群體。1952年,日本議會通過了對《日本公路交通管制法》的修訂,允許更為年輕的駕駛者騎摩托車,鈴木是率先調整產品去迎合年輕消費者的幾家公司之一,推出了排量為60毫升的Diamond Free低端摩托車。同樣地,本田在1952年發布了排量為50毫升的Cub F-Type車型,定位越來越多需要運輸工具而又負擔不起大型車輛的小企業。豐田將摩托車的價格制定在25,000日元(按照當時匯率約合70美金),并且提供了12個月的分期付款計劃。國內公司競相爭奪收入低微的消費者,他們所采取的方式是:降低配件的檔次,升級配送渠道。最終,四大摩托廠商不僅為日本創造了就業崗位,同時還具備了出口到美國和歐洲的能力,在這些市場中贏得一席之地。
在電子消費品行業,松下、夏普和索尼都采取了同樣的模式;汽車行業有尼桑和豐田;辦公設備行業有佳能、京瓷和日立。他們都采取了兩步走的策略,首先在日本國內市場贏得非消費群體, 之后再在海外市場采取相同的策略。
韓國復制了日本的這種模式,像三星這樣的市場創新者對于韓國的經濟崛起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些創新者都曾深入研究過日本的經驗。三星在成立之初是一家貿易公司,但是,三星在1969年成立了一家電子子公司,生產產品以消除國內在娛樂和冷卻技術方面的非消費狀態。三星電子的首款產品是一臺黑白電視機,由三星和日本公司富士通以及三井住友聯合生產。之后不久,三星學習了日本的模式,生產出了韓國第一批低價電扇,后來三星發展到生產低成本的空調。通過不斷地開展市場創新,三星現已成為全球最知名的品牌之一,也成為了對韓國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最大的企業之一。
同樣地,在中國,有市場創新者成功地將本土利基市場擴展成為區域或者全球市場,涉及的行業范圍從耐用消費品到建筑設備。海爾于1984年創立,最初面向中國的非消費者生產迷你冰箱,之后,海爾與德國公司利勃海爾展開了合作,并因此掌握了技術和設備。截止到2011年,海爾憑借著中國市場的經驗,建立了豐富的產品線,摧毀了眾多“白色家電”行業的領導品牌,全球市場份額達到7.8%。類似的還有三一重工,三一成立于1989年,最初只是立足于湖南偏僻小鎮的一家焊接材料廠。三一運用對本土需求的了解和最新的技術進步,為中國繁榮的建筑市場制造出便宜的建筑設備。目前,三一在中國國內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了其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公司卡特彼勒,同時,三一的海外市場份額也在不斷擴大。
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其他一些國家。在智利,政府改革以及蓬勃發展的銅工業備受贊賞,但是市場創新似乎才是智利經濟發展真正的引擎。例如,智利繁榮的農業就是基于市場創造,在此之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時候,處于非熱帶地區的發達國家普遍很少消費新鮮水果和蔬菜。智利的農業出口商改善了種植技術和現代物流,使得一年四季生產供應新鮮商品成為可能。
在印度,很多醫療保健提供商都采用市場創新模式,以使得他們的高質量健康服務變得更加便利。Aravind眼科醫院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給貧困的非消費者提供低價的眼科手術。通過引入市場創新,例如提高醫務人員的利用率,對付費和非付費顧客的服務水平進行分級,Aravind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眼科醫院。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日本的案例,印度的企業正利用他們國內的平臺瞄準海外的非消費者:例如,Narayana醫療保健集團,目前正在籌備開曼群島的分店,目標顧客鎖定為對價格敏感的美國人。并且,印度現已成為健康旅游產業的領導者,每年服務超過100萬的外國人。
在巴西,雖然那兒的石油和木材資源常常引入注目,像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這樣的創新者一直在努力地創造就業機會。與大部分飛機制造商一樣,巴西航空工業公司最初有賴于政府補貼扶持,并且專注生產軍用飛機。但是該公司后來嗅到了民用飛機的商機,開始為國內航空公司生產低成本飛機。現在,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已經掌握了廣泛的技能,創造了廣闊的國內供應網絡,還為幾十家頂尖的國際航空公司生產飛機,其中包括了美國的各大航空公司,例如美國航空、達美航空、捷藍航空以及聯合航空。另一個市場創新的例子是Grupo Multi,這家英語培訓學校開發了一種全新的模式,教巴西人如何說英語,將目標客戶鎖定在外語學習這塊非消費領域。Grupo Multi現在擁有2600個分支學校,創造了2萬多個就業崗位,已培訓超過80萬名學生。
恰當的投資方式
以上的案例表明,通過瞄準非消費群體,創建強勁的、未來能夠擴展到區域或全球市場的本土銷售網絡,將會帶來廣泛的增長機會。以這種方式看問題,就更加清楚地知道資源和投資在發展過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很多表面上看似有價值的發展方式,例如對自然資源產業和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以及常規的國外直接投資等,很少會帶來投資者所期望的效益。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樣的一些投資并沒有創造市場。
經濟學家長期以來都想知道,為什么石油儲藏豐富的國家(例如伊朗、伊拉克、墨西哥、尼日利亞和委內瑞拉)或者稀有金屬資源豐富的國家(例如蒙古、秘魯和俄羅斯)創造了數以千億美元的收入和利潤,但是幾乎沒有新的就業崗位因此產生,國民經濟也沒有因此增長。答案是,發展中國家在資源產業上的投資所帶來的是效率創新,這種創新的目的是低成本高產出。從這些鉆井和煉油廠投入運營的那一天開始,他們的經理人就一直把減員增效當作目標。這符合效率創新的邏輯,效率創新的結果是工作崗位的流失而不是增加。
許多基礎設施項目,例如通訊塔、發電站和道路,都屬于效率創新類的投資。他們降低了本土企業運營的成本,方便企業能夠更好地服務既有顧客,但是他們并不會直接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繁榮。實際上,如果效率創新類的投資不能夠與將目標瞄向顧客潛在需求的投資方式相結合,那么這類投資所產生的利益只會局限在既有的顧客身上,他們的經濟影響也會非常有限。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機構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通常不能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
大部分國外直接投資的終極目的是效率。國外直接投資最常見的一類就是,某個跨國公司開設低成本的工廠,為市場成熟的終端產品提供配件或服務。通常,這些投資都是“流動的”:一旦A國的成本不再具有優勢,如果可能的話,跨國公司就會把工廠搬到成本更低的B國。這些投資來了又走,不會成為增加產量和就業崗位的長期穩定力量。
一些類型的國外直接投資確實能夠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如果該投資支持的是正在海外開拓嶄新市場的產品。一般來說,終端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增長速度要快于效率創新降低成本的速度。這樣的一種投資方式初期需要招納員工為做大做強工廠而工作,之后,公司通過不斷地雇傭新員工來跟上客戶發展的步伐。這一差別就解釋了為什么外國直接投資沒有在墨西哥創造基礎增長,但是在臺灣卻創造了基礎增長。美國在墨西哥的大部分投資都是在成熟的終端市場支持效率創新,例如在汽車制造業、家電業和電動機行業。相反,大部分促進臺灣經濟增長的企業——包括華碩電腦、HTC、鴻海精密工業、聯發科技以及臺灣半導體制造公司——都將效率創新根植于市場創新之內:在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等市場創新產品里采用更加高效的配件或服務。因為市場創新所帶來的增長比效率增加所造成的成本降低率要大得多,因此從廣泛層次看,經濟變得更加繁榮。
如何創造持續增長
鑒于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投資都是自上而下的產物,并且重點都在提升效率上,因此寄希望取得增長的領域最后幾乎都沒有增長。為了未來能夠做得更好,政府和民間應該齊心協力,共同支持國內的市場創新和市場創新者。
也許促進市場創新最為關鍵的一步是:落實能夠加快投資者和市場創新者之間資金流動的平臺和激勵機制。這當中的部分工作僅僅需要對現有的工具進行調整,使其適應投資新興市場所面臨的特殊挑戰。例如AngelList和Gust這兩個網上投資平臺,他們幫助投資者與企業家直接對接,在加快市場創新投資上很有潛力(鑒于他們能夠適應于解決投資者對于合法信托的憂慮),兩家公司目前都已經走向國際市場。像Kickstarter和Indiegogo這樣的眾籌網絡,他們重點幫助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少數族裔進行投資,同樣也可以將目標精準地瞄向市場創新活動。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決策者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從資源所賺得的收入中抽取一部分出來,設立專門致力于市場創新投資的基金。這類基金應該由懂得如何發現和支持市場創新的投資者自主管理。
許多企業家都將精力放在向既有的成熟市場引進產品和服務上,但是市場創新是建立在瞄準非消費即新興市場的潛在需求的基礎上的。為了幫助企業家挖掘到發展中國家大量的非消費機會,必須要向他們提供充足的培訓項目,教企業家如何發現非消費并且預估消除非消費所帶來的利益。這些培訓項目通過與大學和公司合作,應該研究市場創新是如何在相應國家站穩腳跟的,并且發現高潛力的新興技術。現在已經有一些案例,可供企業家學習市場創新的關鍵因素。例如,Godrej & Boyce生產的一款叫做chotuKool的便攜式冰箱,這款顛覆性的產品讓80%的印度農村消費者買得起制冷設備,這展示了創造力和耐心是如何將改變生活的產品帶給市場的這一部分人群的,因為長期以來,在這部分人群眼里,這些產品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對于想要在發展中國家創立業務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來說,一個似乎無法避免的路障就是腐敗,這個問題困擾他們已久。然而,有證據表明,體制性的腐敗可以規避。因此,盡管印度社會的各個階層都高度腐敗,然而印度南部的信息技術公司卻得到了蓬勃發展,因為網絡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可以繞過而無需穿過腐敗的管道。這一原則給世界各地的其它企業帶來了希望。與其把大把的時間花在證書、執照和注冊的申請或者討價還價上,企業的高管不如尋求與具有改革意識的領導人合作,找到容易辦成事情的方式,從而繞過常規路徑上那些各種各樣的腐敗機會。
對于某些體制層面的約束,不要去等體制本身改變,企業家最好自己想方設法解決這一問題,更好地把控結果。例如,雖然傳統的資本市場可能并不會熱衷于投資市場創新,“提成費融資”的理念卻能夠幫助個體戶。在該方案下,企業家無需通過發行傳統的證券或債券募集資金,就能夠面向投資者發行資本。投資者只有等到產生收入時才會得到回報,企業家付給投資者以提成費——一定比例的收入。收益增加,提成費也會增加,直到提成費累積到與最初的本金差不多。這種方式避免了流動性事件的發生,即,變現的機會,當資本市場混亂地組織和監管不力的時候,流動性事件的結果就很難預測了。相反,投資者受益于流動資金過程,他們對于這一過程可以實時監控并且可以進行第一手地確認。
技能型人才比資本更加稀有,為此,公司可以將這一問題內部化。通過開展企業內部職業培訓或者與高校進行密切合作,公司能直接解決這一問題。有個極端的例子,在韓國,浦項鋼鐵公司開辦了自己的大學,專門培養優秀的工程師。本著“你能夠進口煤炭和機器,但你不能夠進口人才”的理念,浦項的創始人樸泰俊率領公司建立了浦項科技大學,提供科學技術方面的教育。該大學一直在國內外的大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創校未滿50年的全球100名大學排名中,浦項科技大學曾位列第一。
清楚地了解可持續增長的原因,在有利的環境中開展業務,再得到有共鳴的決策者的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家就能創造新的市場和新的機會。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只是會帶來生意的成功,還會創造廣泛的就業崗位,還會為他們的國家和同胞帶來強勁持續的繁榮。
【本文首刊于《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2015年第1期。標題為編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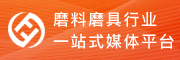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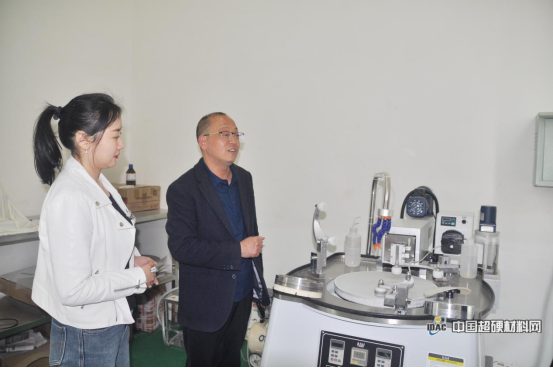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