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魏勇我的外祖父閆秀聲,山東樂亭人。1933年,山東大旱,顆粒無收。外祖父與他兄弟闖關(guān)東到了沈陽。隨后,他們一家人也相繼到了沈陽。為了全家的生計,兄弟2人經(jīng)過老鄉(xiāng)擔保,進入了沈...
作者:魏 勇
我的外祖父閆秀聲,山東樂亭人。1933年,山東大旱,顆粒無收。外祖父與他兄弟闖關(guān)東到了沈陽。隨后,他們一家人也相繼到了沈陽。為了全家的生計,兄弟2人經(jīng)過老鄉(xiāng)擔保,進入了沈陽鐵西一家日本人開的砂紙制造工廠。據(jù)外祖父回憶,當時的日本工廠有十幾個人,他們哥倆是學徒,每天掙二斤玉米面。按當時來講,工作雖然很辛苦,但是為了生計,這種待遇也是蠻高的,基本解決了全家的吃飯問題。開工廠的是日本的夫妻倆,每天早早來到車間門口監(jiān)督工人干活,還一個小個子日本人負責技術(shù),做砂紙的時候負責指導(dǎo)。這個人動不動就要打人耳光,外祖父也常常不得幸免。據(jù)外祖父回憶,當時做砂紙的程序是先將裁切好的牛皮紙(是從日本帶來的)用刷子涂上油漆后,用篩子將砂子均勻的灑在上面。放置在一米見方的木板上,然后一層層地碼放在烘房里進行烘烤。外祖父負責燒煤,當燒到一定的溫度時保持8個小時。砂紙烘干后涼涼后分切成塊,在背面用木質(zhì)刻的圖章印上商標。當時整個砂紙的制作工藝大致如此。
1948年,解放軍攻打沈陽前期,外祖父攜全家逃出沈陽。到了天津,在河西區(qū)一處房子落腳。為了生計,外祖父和我大舅閆紹孟2人便購買了相關(guān)的材料做起了砂紙,并起名“帆船”牌砂紙。當時他們做的產(chǎn)品一上市,便吸引了諸多買家。頭幾批用戶反應(yīng)砂紙脆性太大不好用。但是由于當時沒錢再購買原材料了,為此,外祖父他們便用蒸飯的大蒸鍋將砂紙再進行一次熏蒸。結(jié)果砂紙真的軟下來了,銷路便慢慢的打開了。外祖父背著產(chǎn)品四處推銷,大舅閆紹孟在家負責生產(chǎn)。眼看著企業(yè)就要發(fā)展起來,一場災(zāi)禍悄然降臨了。
1950年年底,人們開始準備年貨了,外祖父他們也加班加點生產(chǎn)。由于疲勞,晚上鍋爐不幸引起了火災(zāi),將整個生產(chǎn)車間焚燒一炬,幸好沒有傷到人,當時消防部門查封了工廠不允許生產(chǎn)了。為了生計萬般無奈,父子倆決定再另尋地方。經(jīng)過朋友的介紹,在當時天津市河西區(qū)千德莊的一片空地另起爐灶,蓋起了生產(chǎn)車間。由于這場大火傷了元氣,外祖父帶著大舅閆紹孟四處籌借又開始了二次創(chuàng)業(yè)。
在企業(yè)逐步走向正軌時,1956年,全國開啟了公私合營運動,天津市機械工業(yè)局組織砂布砂紙手工業(yè)戶開始組建4個生產(chǎn)合作社,我大舅閆紹孟是其中的1家。到1959年,當時區(qū)里干部找到外祖父協(xié)商合營之事。經(jīng)過商議,我們?nèi)野ㄓH屬12人與其他三家合作社共同成立了天津砂布砂紙廠,由個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隸屬天津市機械工業(yè)局第二工具工業(yè)公司。我的外祖父負責廠里銷售,大舅閆紹孟負責工廠的技術(shù),而后又擔任了天津砂布砂紙乙型分廠廠長。
1989年,大舅閆紹孟從崗位上退下來,被天津大港區(qū)一家砂布砂紙制造企業(yè)聘為技術(shù)顧問。我當時29歲,也辭退了市電子元件廠工作,一起來到了大港企業(yè),他一干就是10多年。1992年,全國掀起了經(jīng)商下海熱潮。經(jīng)過再三思考,在家人的支持下,我起照成立了天津市津發(fā)砂布砂紙公司,開始了我人生創(chuàng)業(yè)的新里程。
由于當時全國還沒有國產(chǎn)的紙砂帶,便瞄準了這一領(lǐng)域。我找人設(shè)計制造機械,用竹竿晾曬,當時由于沒錢只買了一軸紙,自己從十幾里處拉回廠里。當時自己又沒錢又沒人,自己起早貪黑,東拼西湊終于做出了環(huán)形紙砂帶的樣品。我?guī)е鴺悠啡チ松虾d撉購S,上海鋼琴廠的同事們看到我的產(chǎn)品后很熱情。經(jīng)過了測試后,很快的與我簽訂了全年30萬的供貨合同。當時我激動的掉下了眼淚,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真是人生的酸甜苦辣無以言表,至今我與上海鋼琴廠的老朋友們依然保持著聯(lián)系,我與他們的友情令我終身難忘。
轉(zhuǎn)眼20多年過去了,我在研磨這個行業(yè)里面摸爬滾打,企業(yè)幾次瀕臨絕境,自己幾次灰心喪氣發(fā)誓再也不干了。但是與研磨事業(yè)的一種情懷難以割舍,思考過后又鼓起勇氣,為了研磨事業(yè)繼續(xù)干下去,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吧!
現(xiàn)在我在天津西青開發(fā)區(qū)購置了土地,建立了近2萬平米的廠房,擁有兩條現(xiàn)代化的砂布砂紙生產(chǎn)線。生產(chǎn)了自己的品牌“圣龍”牌系列砂布砂紙,年產(chǎn)量達到幾千萬平米,產(chǎn)品暢銷全國各地及海外。如今我已到中年,我的兒子魏銘洋大學畢業(yè)后,也到公司幫我打理業(yè)務(wù),我想這也是一種研磨人的緣分吧。
天津市津發(fā)達砂布砂紙有限公司能走到今天,是幾代人的情懷,幾代人的努力,幾代人的夢想。我想,我的外祖父。大舅與我的經(jīng)歷,也是我們中國研磨人歷史的縮影,也是我們國家工業(yè)發(fā)展歷史的縮影吧。 (作者系天津市津發(fā)達砂布砂紙有限公司總經(jīng)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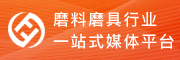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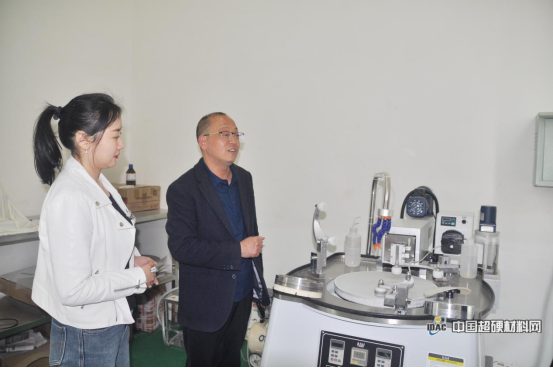







 豫公網(wǎng)安備41019702003604號
豫公網(wǎng)安備4101970200360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