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十年,全球經濟終于漸次擺脫危機陰影,進入復蘇換擋的關鍵階段,并有望借助政策搭配的重心轉移,實現從“脆弱慢增長”向“穩健快發展”的長期狀態轉換。
日益改善的全球復蘇前景,一方面降低了財政風險和債務風險,有望漸次紓解本輪危機以來困擾全球的遺留問題;另一方面則產生了新的風險源頭,換擋風險和金融風險的威脅正在逐步上升。
全球經濟正開啟新一輪復蘇和增長周期。近期,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三大權威機構均表示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持樂觀態度。世界經濟是否已經擺脫危機陰影?在復蘇的過程中,還面臨哪些風險和不確定性?需要進行哪些變革維持強勁而持續的經濟增長?針對上述問題,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程實。
全球經濟進入復蘇換擋的關鍵階段
記者:日前,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18年全球經濟增速調整為3.71%,該數值較7月份預期值上調0.1個百分點。IMF上調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傳遞出怎樣的信號?您如何看待下一階段全球經濟的態勢?
程實:歷經十年,全球經濟終于漸次擺脫危機陰影,進入復蘇換擋的關鍵階段,并有望借助政策搭配的重心轉移,實現從“脆弱慢增長”向“穩健快發展”的長期狀態轉換。我認為,復蘇換擋是強勢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引擎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中美經濟的雙核穩定作用持續顯現,科技進步、政策微調、治理改善、信心趨強和微觀崛起將有力促進全球經濟內生復蘇動能的自我修復。與此同時,復蘇換擋又是危險的,全球經濟增長處于“舊力已弱、新力未強”的狀態轉換階段,換擋風險在短期和長期均廣泛存在,復蘇能否在新擋位長期運行尚存較大變數。強勢又危險的復蘇換擋,是一個量變引發質變、短期銜接長期的自然過程,這個過程勢在必然,唯有全球政策應時而變,快速實現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的重心轉換,這個過程才會導向可持續復蘇的陽光坦途。就投資而言,復蘇換擋的機遇大于挑戰,趨利避害則需要順勢而為、找準方向、把握節奏、“有所為有所不為”。
全球經濟換出“危機慢擋”。時間是撫平創傷的良藥,無論如何百年難遇,金融危機終有淡出歷史舞臺之時,這恰是全球經濟換出“危機慢擋”的時間窗口。根據哈佛大學卡門·萊因哈特教授和肯尼斯·羅格夫教授長時間序列、寬國別視角的學術研究,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的持續期平均為7.3年,在新興市場的持續期平均為10年。自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至今,本輪危機已走過十年,這為全球經濟復蘇換擋提速奠定了基礎。根據IMF的預測,2018年,全球經濟有望實現3.71%的經濟增長,增速不僅高于2008年至2017年危機期間年均的3.33%,還高于1980年至2017年歷史平均的3.48%。一方面,換擋過程強勁有力,2018年的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值較2016年提升0.49個百分點,兩年間的再加速力度為近7年最強,并遠高于0.08個百分點的歷史均值;另一方面,換擋前景值得期待。根據IMF的預測,如若復蘇換擋按照基準情景有序推進,那么,全球經濟2018年至2022年的預期增長均速為3.73%,明顯高于歷史趨勢水平和此前五年水平,增長中樞有望上升至全新擋位。
新興市場引領“換擋提速”。對于危機后的全球經濟復蘇而言,“活力”和“穩定”是稀缺又寶貴的復蘇特質。從兩大陣營對比看,最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在復蘇換擋過程中承擔著支撐提速的關鍵作用。根據IMF的預測和我們的測算,2018年,新興市場有望實現4.85%的經濟增長,增速高于4.54%的歷史平均水平,并較2017年提速0.21個百分點;2018年,發達國家則有望實現2.03%的經濟增長,增速低于2.43%的歷史平均水平,并較2017年減速0.14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未來五年,“新興提速、發達減速”的格局可能還將延續,2018年至2022五年間,新興市場經濟增速有望升至4.98%,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則預估降至1.78%。明顯此消彼長的增減速對比,意味著全球經濟正在經歷從多元化退潮向多元化漲潮的結構異變。2018年,新興市場經濟增速領先發達國家的剪刀差為2.82個百分點,較2017年上升0.35個百分點,2018年至2022五年間的均值則有望繼續上升至3.21個百分點。多元化漲潮過程中,新興市場將引領全球經濟復蘇換擋提速,2018年,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的增長貢獻有望達到77.72%,較2017年上升2.46個百分點,較危機前的2006年上升6.17個百分點。此外,從國別對比看,最“穩定”的中美經濟在復蘇換擋過程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在2017年10月的預期更新中,IMF將2017和2018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分別較7月上調0.1和0.2個百分點至2.18%和2.34%,并將2017年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均較7月上調0.1個百分點至6.77%和6.5%,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4月至今的7次預測中,IMF 對中國經濟增速進行了6次調升,1次調平,這充分驗證了中國經濟超預期反彈的強勁特質。2018年,作為全球最大、最穩定的兩個經濟體,中美經濟對全球經濟復蘇的貢獻總計42.45%,高于歷史平均的35.86%和危機期間的42.13%;其中,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增長貢獻尤為醒目,2018年,中國的貢獻率有望達到32.91%,高于歷史平均的21.3%。
復蘇過程中將產生新的風險源頭
記者:在肯定全球經濟出現明顯回暖跡象的同時,IMF也直言復蘇的過程可能經歷曲折。您認為全球經濟還面臨哪些風險?
程實:日益改善的全球復蘇前景,一方面降低了財政風險和債務風險,有望漸次紓解本輪危機以來困擾全球的遺留問題;另一方面則產生了新的風險源頭,換擋風險和金融風險的威脅正在逐步上升。
第一,狀態轉換面臨“換擋風險”。復蘇換擋本質上是狀態轉換的過程,因此,“換擋風險”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換擋風險”表現為狀態反復風險,即經濟復蘇從低速擋位提升至高速擋位后,新狀態極不穩定,甚至出現被迫再度換回低速擋位的危險。盡管換擋力度是強勁的,但IMF也并未對長期愿景盲目樂觀。2017年10月IMF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名為“尋求可持續增長:短期復蘇和長期挑戰”,標題本身就意味著可持續增長并非觸手可得,在報告序言中,IMF更是直言“復蘇十分脆弱,穩健增長也許并不能持續,許多地區的中期前景不盡人意”。我們認為,狀態反復風險主要是長期結構性風險,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內生性下降、兩極分化多層次加劇、收入增速長期放緩、崗位消失漸成趨勢等,需要全球政策從需求側向結構側換擋才能有效應對;另一方面,“換擋風險”表現為轉換過程風險,即在全球經濟迎來“新開始”的過程中,由于伴生的宏觀“亂紀元”的干擾,狀態轉換遇到阻塞,甚至出現無法完成的危險。我們認為,轉換過程風險主要是短期摩擦性風險,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競爭性貶值、經濟孤島主義、地緣政治沖突等,需要全球政策從割裂轉向協同才能有效應對。
第二,金融風險成為主導風險。由于全球資本市場依然沉浸于寬松狂歡、市場波動性長期處于歷史低位,一旦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正常化進程快于預期,就可能打破暴風雨前的寧靜,導致風險溢價的驟然跳升和資產市場的劇烈調整。這一金融風險已不再是小概率、弱預期的“黑天鵝”,而是逐步逼近、伺機而動的“灰犀牛”。IMF在《2017年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如果上述金融風險發生,預計會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1.7個百分點的損失,并迫使全球重回貨幣寬松時代。
對于這頭“灰犀牛”,雖然難以精確預知其何時撞擊全球經濟,但是把握可能的沖擊路徑、預測潛在的沖擊部位,亦能有效地未雨綢繆,助力風險防控。我們認為,一旦政策轉向觸發全球風險偏好逆轉,那么將首先引發資本市場泡沫風險和新興市場貨幣風險,其形成的沉重風險壓力將主要由新興市場承擔。
首先,資本市場泡沫風險。當前,隨著全球貨幣寬松的刺激效應達到高潮,疊加各國復蘇前景普遍好轉,全球股票市場的估值水平不斷攀升。但是,如果貨幣政策轉向引發金融環境過度收緊,缺少基本面支撐的部分股票市場將首先遭遇估值調整。我們依據宏觀市盈率,考察一國股市漲跌相對于實體經濟表現的強弱程度。從當前時點看,在“G7+金磚” 國家中,各國宏觀市盈率分化顯著。其中,印度、巴西、南非和美國的宏觀市盈率超過1,尤其是印度、南非的年度增幅遠高于其他國家。因此,以上四國的資本市場估值水平已經大幅偏離實體經濟的增長表現,出現明顯的資產泡沫,市場脆弱性正在上升。此外,2018年,如果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金融監管放松力度失當、節奏失序,則可能引發全球性的金融監管競次,導致上述資本市場泡沫風險進一步擴張。
其次,新興市場貨幣風險。除了沖擊資本市場外,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收緊和全球風險溢價的跳升也會增強避險需求,刺激國際資本流出新興市場,進而引致新興市場本幣匯率振蕩。我們選用主權CDS息差水平、外匯儲備總量和“雙赤字”水平對貨幣危險性進行衡量。上述指標顯示,2018年新興市場排名前十的危險貨幣依次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阿根廷比索、南非蘭特、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印度盧比、越南盾、印尼盾、白俄羅斯盧布。當全球資本流向逆轉時,上述國家的幣值穩定預計將受到嚴重沖擊。尤其對于印度、巴西和南非而言,資產泡沫的破裂和本幣幣值的驟跌可能同時出現、相互共振,進而有可能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投資理念需應時而變
記者:根據IMF的報告,今年全球75%的經濟體增速都將加快,這也是全球經濟近十年來最大范圍的增長提速,同時復蘇過程中也蘊含較大不確定性。在這樣的環境下,全球投資者應當如何捕捉大類資產的投資機遇?
程實:展望未來,投資理念需要聚焦“換擋機遇”。大的轉變總是蘊藏著大的機遇,即便風險結構更趨復雜也是可承受的對價。因此,投資理念也需要應時而變:第一,將長期投資的重心從金融市場轉向實體經濟,從波動性套利轉向趨勢性逐利。盡管持續期存在變數,復蘇換擋的結果依舊是復蘇平臺的抬升,這將給實體經濟運行帶來普遍性機遇。第二,借力全球經濟復蘇的動力換擋,把握新興市場相對于發達市場的階段性比較優勢。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印度經濟增長預期被大幅下調,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的經濟增速預期均低于2%,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更顯穩健,經濟增速不斷獲得上調,因此,在新興市場內部,中國的比較優勢進一步凸顯,有望獲得全球資本的持續青睞。第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對復蘇換擋過程中的長短期風險保有高度警惕。在狀態轉換過程中,宏觀“亂紀元”不會永遠伴隨著金融市場的風平浪靜,波動性處于絕對低位的狀態難以長期維系,對高估值市場尤其需要保有審慎。第四,提前布局具有全要素生產率提振效應的活力領域,把握全球政策從需求側向供給側換擋的必然趨勢,充分借力結構性政策的政策紅利。
重點發展石油人民幣等
多元化計價結算體系
記者:在當前的全球風險格局下,為了實現強勁、平衡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需要進行哪些變革?
程實: 2018年,以巴西、沙特為代表,新興市場以及能源、資源出口型經濟體承受重壓,成為財政風險、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的交匯點。石油人民幣等多元化計價結算體系亟須發展,以推動全球貨幣體系的優化升級,支撐全球經濟的穩健復蘇。
從全局視角看,石油人民幣與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建設相輔相成。以“一帶一路”沿線經濟發展的內生需求為動力,以人民幣的貨幣信用為支撐,石油人民幣體系將逐漸形成惠及中國、沿線經濟體、石油出口國的良性循環。第一步,在全球石油供大于求的格局下,石油出口國通過進入石油人民幣體系,能夠優先對接中國位居全球首位的石油進口需求,獲得穩定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第二步,石油出口國的石油人民幣盈余,將逐步回流至中國金融市場和人民幣離岸市場,并由此為中資企業和以人民幣融資的“一帶一路”沿線企業提供資金。第三步,上述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資本輸出,將加快區域內國際產能合作與經濟結構優化,充分激活沿線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同時,人民幣流動性與新興市場的周期高度匹配,也有助于防范新興市場的財政風險和金融市場風險。第四步,沿線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為石油出口國的人民幣資本輸出產生豐厚利得,同時也將從根本上擴大石油需求,開啟新一輪的互惠循環,并不斷鞏固石油人民幣體系。由此可知,在這一循環中,中國將加速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多層次金融市場建設、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和國際產能合作。沿線新興市場將受惠于充沛的資本流入,穩定的區域金融市場以及持續的區域經濟復蘇。而對于石油出口國而言,不僅能夠擺脫美元依賴,更能夠走出石油低價泥淖,獲得穩健的石油出口收入和多元化的資本利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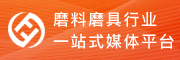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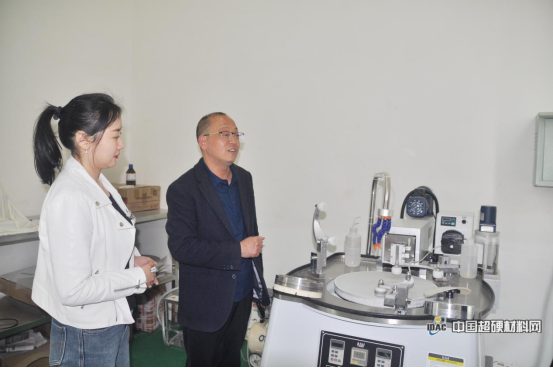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