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產業鏈降價,光伏的又一次歷史性拐點,終究還是來了。
1、歷史大反轉
漲價,2021年整個光伏產業圍繞這一主題展開。
始作俑者是硅料,至于硅料價格大漲的原因,光伏“大躍進”下的供應鏈失衡是問題根本。
當產業整體擴張時,如果某一環節的擴產速度落后,那么必然拖累整體節奏,同時會引發下游對該環節的搶購。2020年是光伏玻璃,2021年則是硅料。
硅料從擴產到落地約1-1.5年,滿產需要2-2.5年,相比之下,硅片、電池片和組件等環節擴產周期只有3-6個月。很明顯,硅料在短期內的產能釋放完全跟不上下游擴產的速度。
更大的問題是,“雙碳”政策給了光伏界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底氣,硅片、電池、組件環節的產能動不動就翻倍增長。為了搶占市場,下游幾家龍頭大廠通過長單鎖定了90%的硅料供應,讓本不富裕的硅料產能更加捉襟見肘,中小企業和新進入者則在剩下不到10%的產能中搶食,把價格推上了天。
2020年12月,致密料價格還在80元/KG徘徊,而在過去一年的時間里,這一數字翻了三倍還多。硅料價格的失控順產業鏈依次向下傳遞,推動下游環節集體漲價。
沒想到的是,轉折來的如此之快。
去年11月底,隆基和中環打響了光伏降價第一槍,連續下調報價,隨后全產業鏈價格跟跌,就連之前滾燙的硅料也繃不住了。
12月22日,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硅業分會發布最新數據,單晶復投料成交均價下滑至23.86萬元/噸,周環比下跌4.94%;單晶致密料成交均價下滑至23.62萬元/噸,周環比下跌5.14%。今年1月5日,硅業分會發布最新數據,硅料價格繼續下探。
事實上,去年三季度后,光伏產業鏈也曾出現價格回調,隨后再次挑起,那這一次還會如故嗎?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需要明確一點,三季度降價有政府外力干擾的成分,而此次降價則是從產業中游的硅片環節主動發起并傳導,是市場博弈后的結果,反應真實供需情況。
其次,把眼光放長遠,光伏產能已經全面過剩。
冷靜下來算一筆賬,按照目前行業規劃的產能,到2021年底,單晶硅片產能就達到380W,2022年進一步提升到550GW,組件、電池規劃的產能落地后也將達到400GW左右。即便是2021年緊俏的硅料,2025年的產能也將達到300萬噸,對應生產超1000GW硅片。
再看一下市場需求,不禁讓人大跌眼鏡。
TrendForce在最新研究報告中指出,2021年全球光伏新增裝機量預計約為150-160GW,2022年同比增長30%,達到200-220GW。而根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預測數據,到2025年,全球新增光伏裝機容量上限也才不過330GW。
換句話說,未來幾年,僅國內光伏企業的產能就將大概率數倍于全球市場需求,這是全面地、絕對過剩!
此輪價格調整或許并不是短暫回調,而是歷史性大反轉的開始。過往的經驗表明,漲的快,往往跌的也急,具體可參考2020年以來的光伏玻璃。
光伏玻璃行情自2020年7月底開始啟動,3.2mm鍍膜價格一度從24元/平米上漲至45元/平米,期間漲幅超80%。但從2021年3月開始,光伏玻璃價格從頂端快速下滑,到五月底,3.2mm光伏玻璃均價已跌至22元/㎡。
從翻倍到腰斬,只隔了不到半年時間。
2、光伏沒有新鮮事
過去二十年,光伏始終處在一個怪圈之中,試圖通過產能擴張來提升競爭力,但動不動就把產能打到全球都消化不了的水平,最終總是難以逃脫“努力擴張,然后破產”的夢魘般的輪回。
“金融危機”“歐美雙反”“531新政”,二十年里的幾次大劫,看似都是“天災”,實則均摻了“人禍”。
2004年,歐洲開始加大對光伏的補貼,以此為標志,國內開啟了第一輪光伏“擴張熱”。各路梟雄跑馬圈地、大干快上,把多晶硅價格從2005年的40美元/公斤推到了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瘋狂程度可見一斑。下游廠商為搶占市場則不得不長單鎖定原料,結果卻是作繭自縛。
2008年,金融危機不期而至,多晶硅瞬間塌方,價格重新回到雙位數時代。后上的硅料產能胎死腹中,下游鎖定長單的企業功虧一簣。
如此慘烈的教訓,光伏人反思了嗎?引以為戒了嗎?
顯然沒有。
2009年,“太陽能屋頂計劃”橫空而出。政策一吹風,產業界又躁動了起來。不只是光伏業內在激進擴張,很多八竿子打不著的企業都來了,有賣水泥的,有做服裝的,用當時一個企業家的話說:“只要有錢就可以整!”
結果是,到2010年,全國建了一百多個光伏基地,有1000多家企業,組件產能達到了35GW。作為對比,當年全球新增裝機量不過15GW。
巨量的過剩產能迫使光伏企業大打價格戰,清倉式出貨,腰斬式降價,最終在2012年引發“歐美雙反”。這一年,中國光伏的對外出口金額直接從225億美元驟降至127億美元,對極度依賴海外市場的光伏企業形成了毀滅式的打擊。
“光伏教父”楊懷進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這多像是一場煙火,砰的一聲,上了天,落下來的全都是灰!”
2018年,“531新政”出臺,明確降低光伏補貼強度,行業再次轟然倒塌。
以硅料為例,2017年末價格還維持在14萬/噸—15萬/噸左右,政策出臺后,價格直接跌掉了一半。
政策刺破了泡沫,但泡沫卻是企業自己吹起來的。在雪崩面前,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根據當時的統計,2017年,以通威、協鑫、中環、隆基等為代表的12家大型光伏企業砸了1000億元擴張。
2017年,國內規劃了20多萬噸的多晶硅產能,在原有基礎上直接翻了一倍。2016年,單晶硅片產能尚不足20GW,而到了2018年,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60GW。
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從沒有從歷史中得到過教訓。
2020年,光伏全行業的投資達到4000億,硅片、電池、組件環節擴建產能超過了去年全球市場的總需求。
進入2021年,在明知產能已經完全過剩的情況下,擴張不僅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根據最新的統計,2021年,光伏行業總共涌進了7000多億,僅上半年的投資額就已接近2020年全年的水平。即便是價格已經高速滑坡的光伏玻璃環節,也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涌進了超400億的資金。
宇宙的本性就是摧毀現有的事物,然后再創造一個類似的事物。早期的草莽倒下了,新生代的草莽又來了。
“愣頭青”不在少數。
比如高景太陽能,上來就規劃了50GW的硅片產能,大筆一揮就是170億,要知道2021年中國全年的裝機量水平也不過如此。
海源復材則更夸張,在深陷退市泥潭的情況下,硬是咬著牙投資105億元建設組件和電池生產線。最新的消息顯示,公司已將投資額提高到了300億元,并宣稱明年投產。
而海源復材目前真實的經營情況是,2021年前三季度,營收不足2億元,凈利潤更是虧損約5000萬元。
一切好似昨日重現,2021年,光伏行業又迎來了一批八竿子打不著的玩家。
有曾經的“拖鞋大王”寶峰時尚,有做水泥的海螺水泥、塔牌集團,還有做化肥的中國心連心化肥……就連以聚焦主業而聞名的曹德旺也忍不住干了一票。
光伏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但大概率的結果是,多數人最終都得折了腰。
3、洗牌,撤退
產業界曾流行一個說法,如果有一個行業通過慘烈來實現價值,那最慘的必然是光伏。
風生水起時,大家一哄而上,都有飯吃,只不過有的吃肉,有的喝湯。但當寒冬來臨時,曾經吃肉的喝湯,曾經喝湯的恐怕很多都得餓死。
不管是久經沙場的“老鳥”,還是初出茅廬的“弱雞”,在“末日審判”面前一律平等。
2008年,國內組件企業達到了400家,金融危機一來,其中300多家被迫關門。“531新政”出臺后半年,有638家光伏企業倒閉,剩下的也大多在茍延殘喘。就連尚德、賽維、海潤、英利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霸主也都相繼命隕。
究其本質,這終歸是一個成本驅動進步的產業,始終遵循先進技術淘汰落后技術、高性價比戰勝低性價比這一鐵律。每當生死存亡之際來臨,總是免不了低價競爭的俗套,關鍵就看誰能挺過去。
過去三年,光伏產業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集中度提升。到2020年,多晶硅、硅片、電池、組件的CR5占比分別提升到87.5%、88.1%、53.2%、55.1%。

▲數據來源:中國光伏行業協會
市場進一步向頭部企業集中,但每一個環節都未形成完全掌控話語權的老大,而是一眾實力不俗的寡頭。
硅料環節有通威、協鑫、東方希望等,硅片環節有隆基和中環,電池片環節有通威、愛旭,組件環節有隆基、天合、晶澳、晶科等。
如此格局,面對即將到來的產能過剩局面,依然難逃價格戰的魔咒。如果說之前的洗牌是“大魚吃小魚”,淘汰落后產能,那這一次更像是巨頭互博。
另一方面,過去多年,大廠們不約而同的迷戀上一體化布局,將觸角伸向了各自的腹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這又為博弈平添了一層迷霧。亂戰之下,是堅守陣地死扛還是收縮陣線、聚焦優勢環節?隨著競爭逐漸白熱化,恐怕所有企業都要面臨這一問題。
總之,一場世紀大洗牌就在眼前,而大資本總是先知先覺。
“531新政”前夕,光伏正干的熱火朝天,但大資本卻在悄悄的撤離。當時有一項數據統計,2018年一季度,機構在隆基股份、中環股份、特變電工、通威股份等四家公司身上就套現了超70億。
2021年以來,以光伏為代表的新能源概念始終站在資本市場的“C位”,但機構又在悶聲出貨。
事實上,早在2021年上半年,機構資金就在悄悄出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高瓴資本退出陽光電源前十大流通股股東。
進入三季度,資金繼續流出,就連隆基、通威這等龍頭公司也被大幅減持。截止到三季度末,共有845只基金持倉隆基股份,總持股量7.78億股,環比二季度末減少了超20%;共有371家基金持倉通威股份,而在二季度末,這一數字為729家,近乎腰斬,持股量也從5.86億股降到了5.26億股,環比減少超10%。
“531新政”出臺后的一年時間里,光伏上市公司總市值曾一度蒸發超2500多億,隆基股份的市值在兩個月之內腰斬,無數投資者飲恨離場。
黑云壓城城欲摧,不知這一次,又會有多少人折戟沉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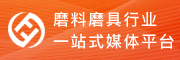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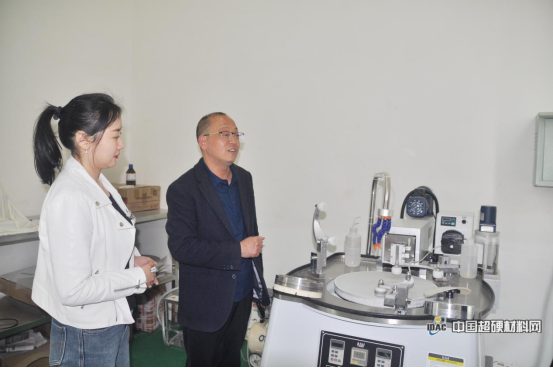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